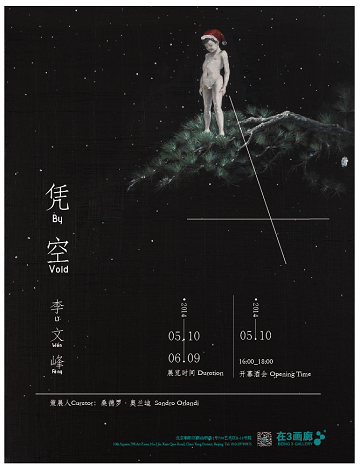1898年,《渝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马尼爱游成都记》的文字,其中记录了一名法国人来到成都城内看到的景象:“甚为宽阔,夹衢另筑两途,以便行人;如沪上之大马路然。各铺装饰华丽,有绸缎店、首饰铺、兑汇庄、瓷器及古董等铺,此真意外之大观”。20世纪初,威廉·埃德加·盖尔更是在一本专著中,直接将“成都”按照字义翻译为“A Perfect Capital”,一座完美的府城。
这些历史描写中的光景,似乎与这座城市现在的面貌别无二致。今天的成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旅游城市,大熊猫和火锅,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当然,如今人们提起成都,一定也必提拍照打卡的胜地宽窄巷子。不过,在成都出生的历史学者王笛眼中,宽窄巷子最有魅力的地方或许并不是那些最新兴建的景点,而是儿时记忆中那间街角的小茶铺。
2003年,王笛来到宽窄巷子,给那里的一些小茶铺拍下了照片。这基本是他成都茶馆研究的最后一趟行程,此前,长期身处海外的他曾数度返回故乡,考察各处的茶楼。他的考察成果,即是如今在中外学界都颇有影响力的《茶馆》。这本书是国内外有志于从事城市史、微观史研究的学者、学生们的必读书。

微观历史的研究,往往具有某些见微知著的特征。今年,著名历史学者卡洛·金斯堡的《奶酪与蛆虫》引进国内,受到读者的热捧。这本微观史的经典就通过一位16世纪欧洲磨坊主的经历,揭示了当时人们脑中的宗教观念图景。而在《茶馆》中,王笛试图呈现的图景,可以说是历史上成都的日常生活气质。
吃茶可谓是成都文化最典型的代表,而茶馆本身堪称一个微缩版的成都,其中折射出不少地方文化的特征。比如,与巴黎、爱丁堡等城市普遍遵循“垂直发展”的规律不同,历史上成都街头的建筑往往呈水平方向铺展,这使得小店铺、居民区距离较近,为发达的街头商贩文化提供了便利。小商贩和店铺的聚集,为茶馆的繁盛提供了配套的服务和往来不绝的人流,这都使得在20世纪初,成都几乎是国内拥有茶馆最多的城市。
在王笛记录的历史中,坐在茶馆里的人也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由于贴近街头,茶馆中可谓“云集三教九流”,除了老成都固定来吃茶,还有赶来谋生、在城里漂泊的外省人常来这里休息。还有一类人会不时地在桌上摆起“茶碗阵”,懂行的人会知道那是成都当地的哥老会组织“袍哥”的接头暗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地方秘密组织虽然与许多历史上的帮派一样与种种暴力行为难脱干系,但却也承担了维持地方秩序的职责,他们常常以茶馆为据点碰面,甚至很多茶馆的老板都是“袍哥”。袍哥们常用“吃讲茶”的方式了断民间纠纷,这几乎成了一段历史时期内,成都地方社会民事调解的特有形式。
街头的茶馆,神秘的袍哥,这些关注社会底层、边缘生活的话题都是1995年王笛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时原本拟定的论文题。囿于史料获取的难度,最后他的博士论文选择了另一个相对好操作的有关街头文化的议题,最终也作为专著出版(《街头文化》)。在赴美攻读博士前,王笛完成了《跨出封闭的世界》,这一研究着重探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在赴美攻读博士前,王笛完成了《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研究“视角还是相对宏观”,关注的话题涉及这个区域内的生态、社会、城市、乡村、经济、人口等多个方面,时间跨度也从清初一直写到了辛亥革命。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研究着重探讨的问题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换而言之,其默认的前提,是用一种积极而正面的态度看待现代化的进程。
经过博士期间的训练,王笛试图超越《跨出封闭的世界》中的研究视野。王笛逐渐放弃了这种多少有些精英主义的历史书写,转而寻求“走向中国社会的底层”,关注普通人的历史。对于身处顶尖大学的学者来说,这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包括斯皮瓦克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曾质疑过所谓“底层民众”发声的可能。相较于可见度更高、多由精英书写的主流历史,挖掘那些被遮蔽的“历史微声”又是否可能?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
对田野调查来说,
共情是必要的
新京报:包亚明的《上海酒吧》可以看作是《茶馆》的一个有趣的对照。成都的茶馆和上海的酒吧,都具有某种公共空间的属性,但一个代表着一种庶民文化,一个则是典型的消费文化象征,风格迥异。我们都知道,酒吧的文化,在当下我们是可以直接去亲身感知到的。但你写的茶馆文化,可能更多已经属于一段历史。我们应该怎样去研究一段历史中的“空间”?
王笛:同样研究一个空间,历史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是不同的。历史学主要是通过文献去研究,去接近那个空间。当然,这种间接性确实让我在研究茶馆的时候怀疑是否能够找到充分的资料和文献。研究初始阶段,茶馆相关的文献非常难找,因此实地考察就成为必不可少。虽然我所研究的茶馆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这种历史不可能完全地消失,它的基因仍然存在于今天,还活在人们身上,文化的烙印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就抹去的。所以我就像人类学家那样孜孜不倦地进行田野考察,也就是到现存的老茶馆中去寻找过去,去拜访经历过旧时代的老人们,做采访和口述,得到了非常多的当年茶馆中的细节。我的田野调查开始于1997年,到2003年基本结束。不过,在那之后,还是习惯性地见到茶馆会做一些调查和照相,包括今年夏天到成都,还搜集了新的资料,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和人物。
回想2017年,我把社会主义时期茶馆的英文版最后定稿交给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并完成了那本书的中文翻译,在书的序言中,我无比轻松地写道,这个课题“现在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关于茶馆似乎在我这里,永远都不会真的画上句号。
新京报:在你看来,历史学的这种田野调查中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你在前往做这个田野调查之前,做了哪些预先的准备?
王笛: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训练主要是文献上的,但是如果要进行田野考察,就应该学习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时候,我除了在历史系修两个方向,还在人类学、政治学各选了一个方向,这四个方向的共同学习,开拓了我的视野,具有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准备,特别是为田野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样第一次走进茶馆的时候,就完全不会手足无措。
当然,社会学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已经对社会学进行过系统的学习,在四川大学任教时,甚至还开过社会学的课程。社会学家很看重田野中的各类数据,我曾经也设计过问卷,试图在茶馆中收集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但是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我把重心放在考察个人在公共空间的活动,公共空间中潜藏的政治、经济结构,又如何影响人们使用这个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使用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等等问题。除了采访老人之外,有一段时间我就整天坐在茶馆里,以一个茶客的身份去和来往的人们交谈,并观察和记录人们的行动,其实这种方法,犹如把自己置身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场景之中。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过去在学术研究中,我总是试图与我研究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种站在研究对象之外的态度,也不能绝对化。要打动我的读者,让读者理解我的思考,“共情”也是有必要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所研究的课题或者对象不能打动自己,我们怎么能奢望打动读者呢?所以在最新的一本书里,我把很多即时的感受融入历史的书写中。我把自己放到历史的场景之中,并发表一些议论。这些议论,既表现了我对历史的思考,也有现实的关怀,大概有点《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的味道吧。当我把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和我“站在历史之外”的写作是不一样的。
新京报:在整个做田野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最深的经历是什么?
王笛: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对茶馆研究的田野考察基本结束于2003年。不过田野工作留下了一个职业习惯,只要我回到国内,看见茶铺就一定会拍照。2015年秋天,为了给那本社会主义时期茶馆的英文专著配图,我到了很有名的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拍了大量照片。2019年夏天,我随一部关于民国川西乡村故事片的导演和制片在各处选景,又去了那家茶馆,顺便又拍了不少照片。当我去年在整理那些照片的时候,不经意间发现两张相隔四年的照片中,都有同一位老人在那里打扑克。这令我感到十分兴奋,当时就突然有一种感觉,这里面可能有故事。由于疫情无法回到内地,于是请了一位川大的研究生去那家茶馆,看能不能找到他,居然第一次去便找到了他。
今年夏天,我终于回到成都,继续进行这个还没有完成的故事,又去了观音阁。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仍然在那里打扑克。这个发现和寻找这个老人的过程,真是非常的奇妙,我有那种时间凝固了的感觉。外边的大千世界,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但是这家茶铺和那里的茶客们,却处变不惊。正如我在给《那间街角的茶铺》画的一幅老茶客的插图题记中所写的:“我是一个老茶客,每当我来到这里,就会感到气定神闲,像回到了家一样,其实,茶铺犹如我的半个家,因为每天我在这里度过我的大部分时间。如果我一天不来,我就会觉得似乎少了一点什么,就会六神无主。在这里,哪怕茶碗里波澜翻滚,茶桌上风云变幻,对我来说,也不过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发现和寻找那个老人的经历,我就写不出上边的这些文字了。

从《街头文化》到《茶馆》等一系列作品中,我反复试图论述的是,有很多我们视为已经消失的“传统”,其实仍然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一个商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总是容易盯着那些变化了的东西,却常常忽视了文化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恰恰需要深入生活的细节之中和接触具体的人才能向我们显现出来。
02
茶馆所代表的慢节奏生活的独特价值
新京报:在围绕茶馆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中,感觉茶馆就像是一个微观的世界,但它能够折射出更宏观的一个区域的文化。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觉得茶馆所代表的这种西南地区的地方文化呈现出什么特点?
王笛:的确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那间街角的茶铺》中,花了不少篇幅讲生态的问题,包括地理、交通、水源、出产等等因素,都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模式,所以我在书中阐发了“成都茶铺多的最根本原因是生态”的观点。
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成都媒体发表不少文章批评所谓的“盆地意识”,这个词本身其实带有贬义。当时的人们大概认为,成都人思想保守,生活节奏太慢。同时认为,茶馆吃茶本身象征的这种闲逸,也是消极的,不利于现代化的。当时文化精英们习惯拿深圳速度作对比,认为成都人身居内地,目光短浅,不思进取。
其实,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城市的文化没有“自信”。但是有趣的是,成都普通人其实以这种文化为自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衍生的社会问题增多,曾经的批评者逐渐发现了这种慢节奏生活的独特价值。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的并不是怎么给生活提速,而是怎样让自己生活的压力更小一些,所以成都的精英管理者们也不再因为这种文化而感到自卑,而是有意识地去推动享受生活这样的一种理念,打造一个宜居的城市形象。

王笛: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场合都有人提出过。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确实是我这一系列的作品中关心的重点,我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时,认为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积极”的发展。这种精英主义的观念自“五四”之后,基本深入人心。后来我的学术发生转向,从底层观念来看历史,其实就是把视点转移到大众文化上来,反思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丢失了什么,又有什么值得警惕。我并不赞同“美化”的批评,在《街头文化》《茶馆》和《袍哥》中,我都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社会冲突乃至暴力问题。其实社会和文化本身是复杂的,也自然存在和谐和冲突两方面的对立,在我的研究中,两方面都有充分展示。
现代化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总会往前走,旧的生活方式会更新,比如城市设施、景观、娱乐休闲方式都不可避免地改变。我希望提醒的是这种变化的速度,是不是太激进,太急功近利,“一窝蜂”地变,翻天覆地地变,会带来怎样的消极后果?我们太渴望变,甚至是剧变,但往往不是按照事物发展本身的逻辑,把一些本来应该保护的东西抛弃了。有些地方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开发肯定是成功的,但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却是失败的,因为真正的有价值的老建筑、老街区没有了。作为历史学者我们既要承认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也要负起我们的责任,即提醒大家更多地关注那些不应该被迅速抛弃的物质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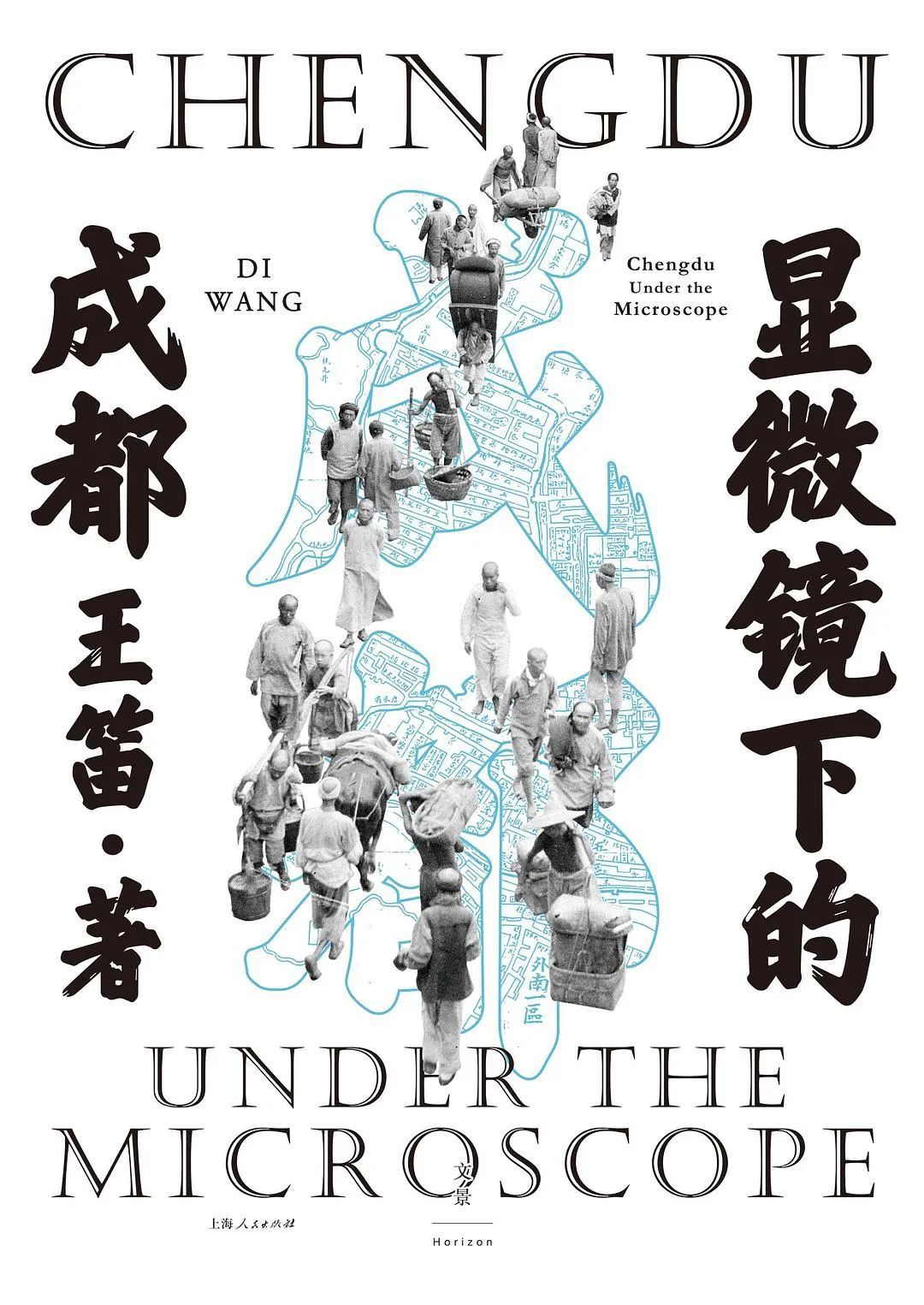 《显微镜下的成都》,王笛著,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
《显微镜下的成都》,王笛著,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
03
茶馆是一个“公共空间”吗?
新京报:在史学界围绕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曾经有过很多重要的争论,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你在茶馆的研究里其实也触及了这个问题。虽说在你看来茶馆具备了一个满足大家“平等交往”需求的公共空间的特征。但通过你自己的记述,我们也发现,单一茶馆内部也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同的茶馆也有着阶层的分化。你如何评价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特征?
王笛:首先茶馆是一个物质的公共空间,就是说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空间,普罗大众、三教九流都能在那里自由出入和开展公共生活。其次它也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空间,这是从比较抽象的意义上来观察的。人们在此进行社会交往,议论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国家的许多政策也直接作用于这个空间。同时作为地方帮派组织的袍哥们在这里也有着自己的“茶馆政治”,比如用“吃讲茶”等方式解决邻里纠纷,这基本上充当了基层的诉讼调解。
我认为,无论是从中国传统的“公”的概念,还是从哈贝马斯的概念出发,茶馆都可以认为是一种“公共领域”,在茶馆中有着极为明显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为了争夺空间展开的博弈。国家利用这个空间施行控制、宣传,各个社会组织和人群则争取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那份自由。当然,茶馆展现的这种公共空间的文化和西方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
新京报:在这几本书当中,你都旗帜鲜明地点出自己的这些研究大体上都属于微观历史的范畴。相对于宏观历史的研究,微观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可能更为多样。我注意到你在《茶馆》《袍哥》中,都用到了图像、文学等多种类型的史料。对于微观史、城市社会史研究来说,对史料有怎样的要求?如何辨析、选取史料?
王笛:微观历史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资料的困难。如果我们研究思想史、政治史,以及政治人物、战争、事件、国家和意识形态等等所谓重大课题,我们有比较系统的资料。然而微观历史是关于普通人的历史,而过去中国历史学对普通人根本不关心,认为研究他们是没有意义的,这就造成了我们今天要研究这些群体,研究日常生活所面临极大的困难。在西方,特别是研究中世纪的欧洲,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有宗教裁判所档案,那些事无巨细的审讯记录,成为微观史挖掘的金矿,所以微观史从意大利和法国产生,也就不奇怪了。
要想写作中国的微观历史,寻找资料就非下苦工夫不可,就是从档案、地方文献、报刊资料中去一点一点地挖掘和筛选。正如你提到的《茶馆》《袍哥》这些研究,资料的来源都非常广泛,但是又非常零散。虽然也有大量资料来自档案,但是档案馆中从来也没有专门的茶铺的全宗,必须从浩如烟海的各种记录中去耙梳。除了通过田野考察去弥补,有的时候甚至还不得不使用文学的资料。
通过千辛万苦把资料收集到手之后,我们还面临着怎样选取、使用以及解读资料的困难。不能说到手的资料就是记录了真实的历史,在使用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资料形成的过程,谁记录的,怎样保存下来的,这个资料是否存在偏见和歪曲等等问题。我从来就认为,资料只是一种文本,而不是历史本身,要转化为历史还必须经过我们的解读、建构叙事以及分析。而且每一个研究者,对一条资料,完全有可能给予不同的解读、建构不同的叙事和做出不同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的资料,很难有完全的共识,我们甚至不能奢望每一种描述都是准确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些记忆所展示的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反映了真实的社会面貌。当然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分清记载和历史本身的界限和距离,在使用这些资料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特别是要考察这些资料在多大的程度上歪曲了、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直接反映了民众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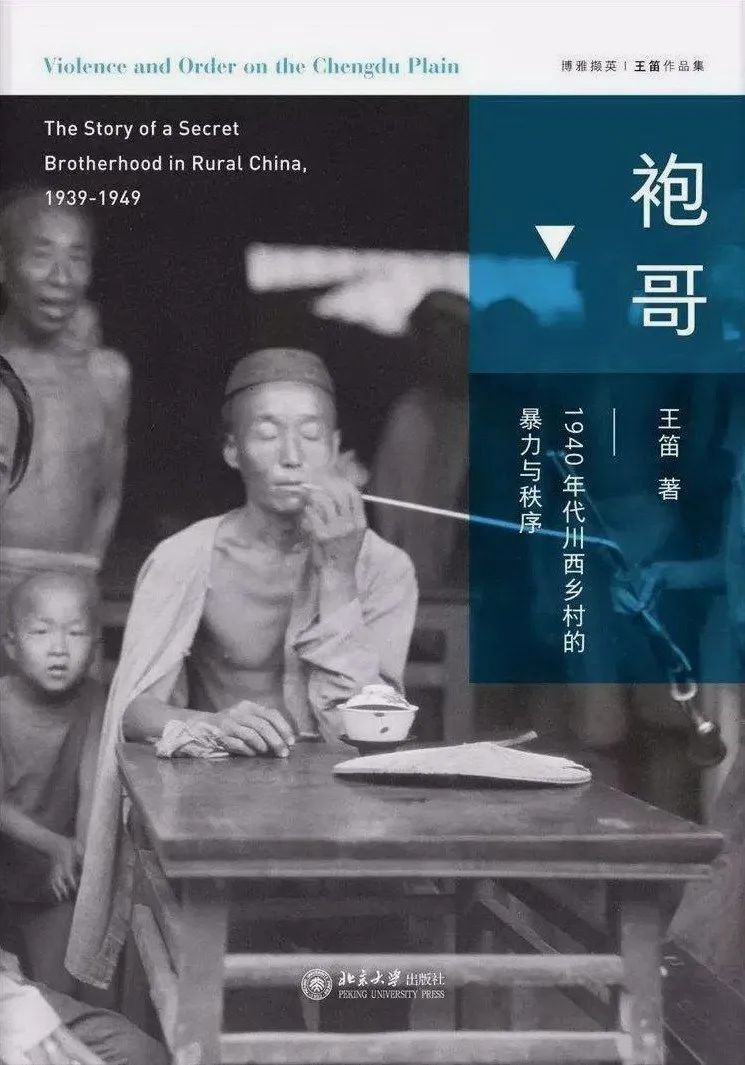
王笛:的确,在这本书里面,我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讲抗战时期的茶铺的日常生活,描述了抗战爆发后,许多逃难文人在成都茶铺里如何找到了一丝慰藉,战乱中人们如何还存在着信任,小商业为什么还是城市的经济支柱,穷人也有在茶铺里休闲的权利,妇女如何在茶铺中受到排挤,茶铺如何就是一个公共论坛,以及国家在战时茶铺中的角色,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反映了哪怕就是在那个动荡的时期,茶馆仍然起着稳定人心的作用,仍然能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服务。
其中我特别讨论了茶铺中关于“清谈误国”的争论。抗战爆发以后,大量的人口来到成都,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甚至相当吃惊,发现为什么现在国家在危急之中,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但是成都的茶馆的生意还是这么好,坐在茶铺里无所事事,这引起了精英的批评。我指出,这些批评茶馆的人,只看到了茶馆的表面,其实茶铺完全超越了一个单纯的休闲空间,各种人物在茶铺中活动,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有的是为了谋生,有的是为了做生意,有的是休闲,有的是社会交往,还有各种社会组织在那里活动……人们在那里可以自由使用公共空间。可以想象,那个时代,如果没有茶馆,人们到哪里去寻找能够同时具有如此多功能的地方呢?茶馆是为各个阶层、各个人群服务的,无论是下层民众,还是地方精英,甚至国家也利用茶馆发动民众加入抗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茶馆就成为了一个政治的舞台。
中华美网责编/李睿 编审/王刚

 中华美网首页
中华美网首页